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陈龙川传》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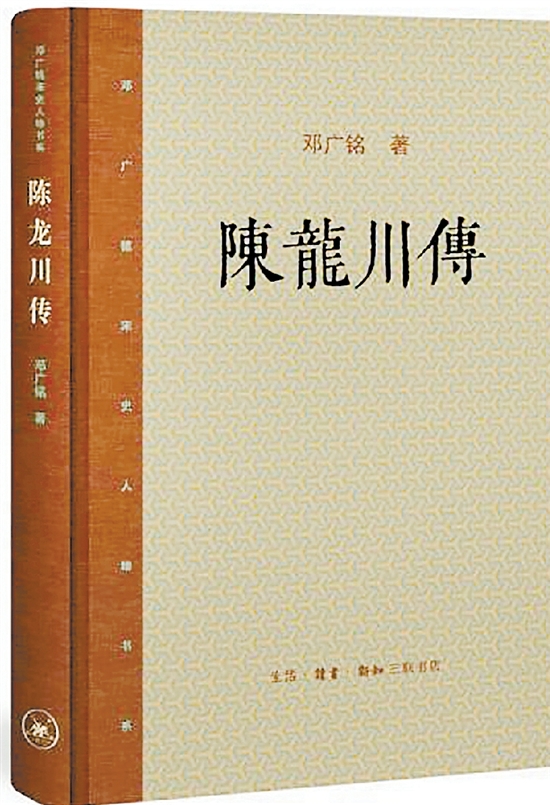 |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陈龙川传》读后感
□赵丹
读书札记
近日偶读邓广铭先生《陈龙川传》,掩卷而思,不禁让人重新审视陈亮其人,乃至整个南宋王朝。许多年前,我曾闲翻《宋词选》,依稀记得陈亮其人,只知陈氏为婺州永康人,南宋状元,豪放派词人,却未曾将其词作铭刻于心,至今思来,不免惭愧。
南宋王朝偏安东南一隅,南渡之后,故土待复。王庭的统治者本该励精图治,光复山河,却不承想皇帝苟且偷安,士子们未敢言战,朝野一片主和之声。整个大宋王朝理学泛滥,“关闽濂洛”之学大行其道,读书人莫不趋之若鹜,理学家们大谈“天理性命”“内圣外王”。试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行将灭亡,儒生们却在高谈阔论,妄图改造民心,岂不可笑?后来王朝的覆灭更是证明了这群儒生的天真。
陈龙川便生于这般时局之中。时势造英雄,风雨飘摇的乱世理应是陈氏走向英雄之路绝好的环境。可事实上,他仅是不断地与风车做斗争的唐吉诃德罢了。
陈亮天资聪慧,自小饱读圣人之书,长成后屡次参加科举,都败兴而归。陈氏并未钻进理学的“牢笼”,而是走向了迥异之途——经世之学。这或许是浙东这块土地所特有的禀性。后世的学者将陈氏的思想概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字,确能反映其一生的言行。他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危难的时局,他曾屡次上书王庭,力主抗金,换来的却只有讥哂和石沉大海。他甚至当着大臣的面痛诉:“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可偌大个王朝,有几人清醒呢?又有谁听其慷慨陈词呢?微斯人,吾谁与归?科场失意,进言遭弃,不禁让他心灰意冷,归隐乡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陈氏注定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包羞忍辱是男儿”,他将荣辱置之度外,仍然特立独行,以至于遭人忌恨,数度被谗下狱。
陈亮一生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莫过于与朱熹的论辩,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尊重朱熹,却不肯赞同其说。两人的文字交锋、思想抵牾曾让朱氏甚为不悦。“经世之学”与“性理之学”孰是孰非姑且不论,陈氏这般坚持己见并身体力行之人,尤其让人钦佩。晚年,他不顾体弱多病,亲赴金陵,考察石头城的地胜形迹。返乡途径临安时,再度上书朝廷,陈言抗金安邦之策。陈氏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唯有与金华吕祖谦亦师亦友亦兄的情谊让其感到温馨不已。东莱先生是陈亮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陈氏每书一文必先呈送于吕氏的案前,每有苦闷之事,便与这位兄长促膝长谈。天妒英才,东莱先生不幸英年早逝,这让陈亮伤心不已,在祭文中发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的哀叹。
东莱的离去让陈亮更加孤独。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太多的磨难并未让他消沉,反而激发了他更旺盛的斗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陈龙川举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可惜还未上任,次年即在家辞世,享年52岁。造化弄人,一生的夙愿即将实现,正要施展抱负之时,却驾鹤西去。功业未遂,只能在另一个极乐世界里收拾旧山河了。
命运如此乖戾,让人唏嘘不已。
长歌当哭,哭陈氏龙川。

 浙B2-20100419-2
浙B2-20100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