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豆肴
母亲的豆肴
□胡梦姣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即使是在“无米”的岁月,她也是一位巧妇。她制作烹饪的各种豆肴是我家餐桌上的美味。豆子经过母亲种植、采摘、制作、烹饪等工序,变成佳肴,饱胃暖心。
母亲种豆子从不占用规整的田土,都是种在田坎边、菜地边。谷雨时节,在田间地头的空隙处挖出一个个小坑,间距约三四十厘米。小坑里放四五粒浸泡过的豆子,草木灰做底肥,然后盖上泥土,略微压紧,免得被鸡鸭或田鼠吃掉。有春雨的滋润,春光的普照,豆子很快发芽、长大,繁茂似一棵棵绿色小树,这时可以间苗。6月至7月,淡紫色小花像一只只小蝴蝶停在绿叶间;7月至9月,那些绿色枝条上就会慢慢长出绿色的豆荚,像孕妇一样,慢慢显出饱满的豆型;9月至10月,豆子成熟时,豆荚和植株变成深褐色。
收豆子是辛苦的力气活。成熟的豆株粗硬、高矮不一,一般用锐利的铁镰刀将整株豆从根部割断。然后捆起来挑回家,放在禾坪摊晒。待豆荚和植株晒成枯褐色,就用木棍扑打,或脚碾踩,让豆子从豆荚中脱离。棍棒打不下来的豆子还得用手一个豆荚一个豆荚剥豆。这些活都是父母干的,他们的双手常常会被硬硬的豆荚和枝条割伤、刺伤出血,手指上白胶布缠了一道又一道。
豆子晒干后收藏,需防虫防潮防霉。小时看到母亲将晒干的豆子包好放在装有石灰的坛子里保存。如今,她在小口径的玻璃瓶或饮料瓶中密封保存,晴天经常拿出来翻晒,避免虫蛀霉变。
母亲给我们做过的豆肴很多。那时候,家里人多米少,母亲经常熬豆子粥,以豆子为主,加少量米,煮得很黏稠,很饱肚。青黄不接时,她就发豆芽菜,清炒做菜,盐炒豆子给我们当零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有石磨,母亲会磨豆浆、做豆腐脑给我们吃,还会打豆腐,用来做霉豆腐和香干。记忆最深的就是磨豆粉,母亲推磨,我随着转磨空隙添豆。豆粉磨好后,母亲用盐炒熟,放在别人给的空麦乳精罐子里,让读寄宿高中的我带到学校加餐、补充营养。
我们成家立业后,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进入老龄的父母仍闲不住。他们还是会种豆、烹饪豆肴。四季饮料是豆浆,清凉解暑绿豆稀。八九月份,是青皮豆最好吃的时候,这时摘下的豆荚呈青绿色,很容易剥开。里面是一粒粒饱满或扁长椭圆状或圆形的豆子,如一颗颗绿色珠子,晶莹、亮丽、鲜嫩,散发阵阵清香。母亲的青皮豆炒肉泥是我们最喜欢的下饭菜,青皮豆油光发亮,白色蒜泥、红辣椒末、酱黄色肉泥、绿色葱花点缀其中,妥妥的色香味俱全。这盘菜一上桌,我们不是用筷子夹,而是用调羹一勺勺舀,拌饭吃,个个吃得嘴巴吧唧吧唧响,次次光盘,颗粒不剩。
青皮豆再成熟一点,颜色呈鹅黄,嚼劲足,豆味浓郁。这个时候,母亲煮的五香毛豆就成了我们的吮指食物。摘下的新鲜深绿色豆荚洗净,加五香粉或八角桂皮、陈皮、辣椒、姜、蒜、盐,加水同煮,豆熟捞出即可食用。看着我们贪吃的样子,母亲总是笑眯眯地说:“喜欢吃,下次再多煮点。”
每年腊八节,母亲都要做腊八豆,她将黄豆煮熟至绵而不烂,然后捞出摊凉,再装进布袋子,布袋用棉絮或稻草包裹好放在盆、桶、缸里,加盖,20℃左右保温,2天至3天后黄豆发烫,发酵长出白霉,取出摊凉,把豆子倒进干净的盆子里,按一定比例加食盐、白酒、辣椒末、生姜末拌匀,装瓶或坛子,密封十天半个月即可食用。鲜香的腊八豆不论是煮、蒸、炒都行,与扎鱼、扎鸡、扎鸭合蒸,那是绝配,闻着就流口水。
大年三十,腊八豆蒸腊味、豆沙八宝饭是我们家团年饭餐桌上的标配。而黑豆当归红枣(或蜜枣)煮蛋是我们守岁的夜宵。春节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不管你饿不饿,母亲都要给每个人端上一碗黑豆当归红枣蛋,她说这个滋阴补气血,来年生活甜甜蜜蜜、圆圆满满。
吃着耄耋母亲用汗水和爱心烹饪的美食,咀嚼出幸福之余,更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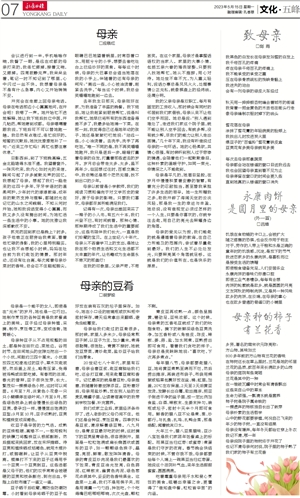
 浙B2-20100419-2
浙B2-20100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