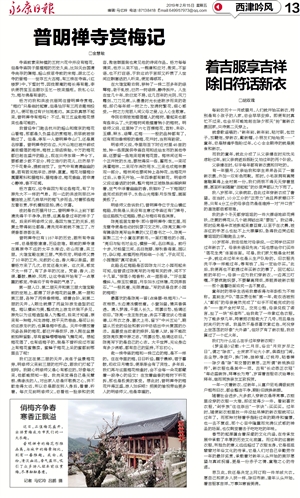着吉服享吉祥
除旧符话新衣
□胡双瑰
每到农历十一月或腊月,人们就开始买新衣,特别是有小孩子的人家,总会早早安排。即便有时真忙不过来,也会尽可能地赶在除夕那天“抢”套新衣裳回家,只待第二天穿上。
就像歌谣唱的:“新年到,新年到,贴对联,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戴新帽,小朋友们哈哈笑……”童年,总是掰遍手指盼过年,心心念念期待的就是美食和新衣。
而我的童年,就此分成了从父亲健在时无忧无虑盼过年,到父亲病逝后既盼又怕过年的两个阶段。
父亲健在时,似乎每年都有新衣裳和好吃的。
有一年腊月,父亲给我和孪生弟弟各买了一套新衣裳,外加一双彩色雨靴。那时,小毛孩拥有高筒套鞋算得上全村第一份,我们俩恨不得天天穿着显摆,甚至听到隔壁“滋啦啦”的炒菜声都以为下雨了。
我八岁那年,父亲病故,自此过年穿新衣成了奢望。在当时,10分工分的“正劳力”尚且养家糊口不易,只有4分工分的母亲自然是连维持一对“开口货”的温饱都倍感艰难。
我的多个冬天都穿姐姐的一件大襟绿地碎花棉袄,泛黄的棉花从几个破洞钻出来“要饭”。我记得,那时经常是半夜被揪起来磨豆腐,以至于在次晨,被冻红的手怎么也扯不上大襟襻扣,急得我边哭边趿着姐姐的旧鞋跑去上学。
10岁那年,我怯怯地对母亲说,一位同学已买好过年新衣了。母亲未语泪先流:“妈也想给你们买件‘落花生壳’体面体面。可是,我们家欠粮是全村第一多,就这点过年米也是从生产队赊的。旧衣服洗洗干净一样能过年,等有钱了,妈一定给你买。”此后,我便再也不敢提过年买新衣的事了。回忆起以前的年初一,母亲一边为我们穿新衣,一边再三叮嘱,不要疯跑玩耍,不要攀高爬低,弄脏弄破新衣服……那个温馨场面终究一去不复返。
童年时的艰辛生活将我磨练得与年龄极为不相称。直到生产队“落实责任制”第一年,做农活被别人“鄙视”的母亲竟然完成了“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亩产全村罕见。交完公粮,母亲兑现了诺言,扯了一块“标准布”,给我做了一件紫红色衣服。为了能多穿几年,特意把衣服做大了几号,而且是当时流行的方领。我虽然不是很喜欢紫红色,何况穿上空荡荡的好像“大外婆”,但好歹有了新衣服,我总算过了一个红火年。
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过年穿新衣呢?
《梦粱录》记载: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订桃符,贴春牌……除夕是“除”有交替的意思,正所谓“新桃换旧符”,新衣服也是其中一项。古有“长幼悉正衣冠”“卑幼盛装饰,拜尊长为寿”,岁首着吉服依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
一年一次着新衣、过新年,从富户尼毛绸缎到贫户粗布旧衣,都会整洁干净,期盼旧貌换新颜。
随着社会进步,大多数人穿新衣是寻常事,衣柜里没穿的衣服一大堆,却还觉得少一件。看到喜欢衣服,“剁手族”往往祭出“一字诀”:买买买。过年时,随便到衣柜里找一件没扯吊牌的新衣服就可以过年了。而那种对掰着手指盼过年的期待和憧憬,也一去不复返,那个心目中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神圣的场面,也仅剩变着法子吃吃吃的年味。
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过年的这套新衣服,所担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衣服本身,它是祖祖辈辈对年俗文化的传承,它是人们对自己辛勤劳作一年的最好奖赏,承载着对新年从头开始的美好愿望与真诚祝福,更是一份赤子之情、童稚之心的传递。
思及此,我还是决定上网订购一件羊绒大衣。愿自己和家乡人民一样,除旧布新,猪年从头开始,着吉服享吉祥,万事如意皆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