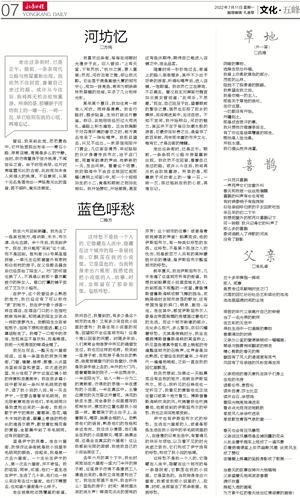蓝色呼愁
蓝色呼愁
□杨方
我在六月回到新疆。我先去了一些其他地方,喀纳斯、禾木、布尔津、乌伦古湖。半个月后,我来到伊宁。现在,我只能用“来到”这个词,而不是回到。胜利街153号某座居民楼,一单元左边那套窗外有枣树和白杨树的房子,在父母搬去昌吉后已经卖给了陌生人。对门的邻居也换了人,不再是以前那个喜欢戴披巾的胖女人。巷口打馕的铺子变成了艾及尔小超市。
在伊宁,这个我曾经多么熟悉的地方,我已经没有了可以称作“家”的地方。我在伊宁像个游客一样住酒店,在酒店门口的小饭馆吃椒麻鸡拌面,和同桌的陌生女孩点一样的菠萝汽水。我朝陌生女孩举起瓶子,但她不想和我搭话,戴上口罩结账走了。我喝了一口瓶中的液体,发现其实不是饮料,而是啤酒。我把一大瓶微苦的啤酒全喝了。
我无处可去,一整天在六星街闲逛。这是一条蓝色的民族风情街,门窗、墙壁、楼梯、廊檐,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依次递进的蓝,充分体现了伊宁这座边境小城的诗意和浪漫美学。我在很多篇小说中都写到一条叫羊毛胡同的巷子,读了我小说的人说,有一天去伊宁,一定要去看看羊毛胡同。我无限歉意地告诉他们,羊毛胡同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一条街。我把分散于伊宁的果树、葡萄架、杏花,唱木卡姆的老者,藤蔓上悬挂的柄很长的维吾尔葫芦,散发着玫瑰花香的黄昏,全都集中到了羊毛胡同。还有民居的蓝。
蓝是伊宁的灵晕。走在六星街,我惊讶这条街就是我小说里羊毛胡同的颜色。说起来,我是第一次去六星街。一个生长在伊宁的人,第一次去六星街,并不奇怪。我的姐姐、同学、邻居,他们一直生活在伊宁,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也一样从来没有去过六星街。他们不需要去,也知道六星街是什么样子。
走在被果树浓荫覆盖的街道,我问自己,我看到的,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隔多年后,人们常常会相信梦中所见的确曾发生过。我也犯这样的毛病。我来到一座房子前,发现房子是如此的熟悉,临街玻璃窗内的白色窗纱,仿佛是我亲手挂上去的,半开的大门内,搭着葡萄架的院子,一半在荫凉中,一半在阳光下。给人一种一分为二的清晰感,仿佛我的思维一半在虚构的小说里,一半在真实中。土墙边摆放的天竺葵正开着花。浇花的铁皮水壶,完全是我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形状,摆放的位置也跟我小说里一样。葡萄架下的土台子上,坐着聊天、喝茶、抽莫合烟的人。我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性格和命运走向。我没法分清楚,他们是坐在我的小说里聊天、喝茶、抽莫合烟,还是坐在真实的六星街?这让我感到无限的困顿,我被我自己的小说给困住了。
去年六月的某个下午,我长时间地站在六星街一座大门半开的房子前,这座房子仿佛不是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是我立体地虚构出了它。我站在那里不走开,我在听什么?蓝色的房子?时间?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芬芳?这个城市的往事?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帕慕克说,他的伊斯坦布尔,有一种类似呼愁的东西。这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某种朦胧状态的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前年夏天,我在伊斯坦布尔,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所有的街道。我想找到帕慕克小说里卖钵扎的人,找到那些不规整的一夜屋,黄昏博斯普鲁斯海峡成群飞舞的鸥鸟,夜晚降临时在城市游荡的野狗,还有帝国残留的拱门、喷泉、剧场、浴池。走在其中,感觉伊斯坦布尔人像是在帝国倒塌的废墟里过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个城市新建的部分,无论多么现代,多么繁华,依旧闪耀着呼愁。尤其是傍晚时分,我坐在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座桥上,听见蓝色清真寺宣礼塔上响起的传遍整座城市的召唤声,这声音是如此熟悉,它曾经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一遍遍地响起,之后一直在我的回忆里飘荡。
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天帕慕克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就在伊斯坦布尔。那么,我听见的召唤他也一定听见了,我看见的黄昏他也正站在窗口或某个地方看见。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风,吹拂着我也吹拂着他,他感受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我也正深深地感受到。
伊宁也有伊斯坦布尔式的呼愁。生活在六星街的人,或者是那些生活在我小说中的羊毛胡同里的人,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有看得见的快乐与烦恼,以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之哀伤,它们构成了伊宁独有的呼愁,构成了我小说的格调。
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
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