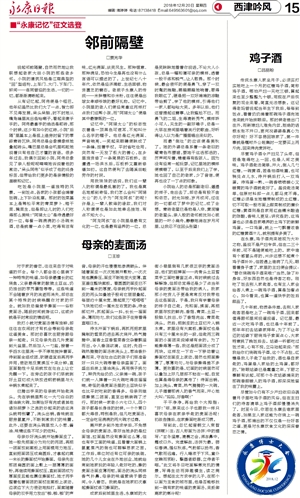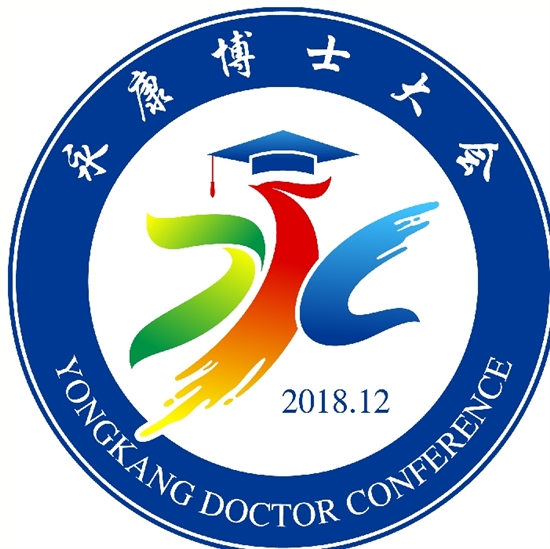 |
■“永康记忆”征文选登
邻前隔壁
□贾光华
说起邻前隔壁,自然而然地让我联想起老家大田小院的那些老乡邻。小院的建筑风格是江南典型的“回”型结构,上车门、大门、下车门、轩间——连同曾经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渐渐清晰起来。
从有记忆起,阿伟便是个哑巴。他年纪虽然比我们大了一点,智力却不见得发展,呆头呆脑,时不时地从嘴角缝里流出些哈喇子,看起来傻乎乎的。阿伟最拿手的绝活是砌砖,那个时候,还少有如今的红砖,小院“后隔”里基本上是祖上造房时留下的零碎青砖瓦块,阿伟总是会像模像样地叠起砖头,嘴巴里总是会叽里呱啦地说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言语。很多年过去,我偶尔回到小院,阿伟总像见了亲人般呢呢喃喃地诉说着他的激动。“呆头阿伟”似乎成了他的终身标签,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亲情般的温暖和记忆。
吃饭是小院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一到饭点,各家的小孩都会端着饭碗,上下阶沿乱窜。那时的饭菜基本上是稀松平常的青菜萝卜、梅干菜、腌菜生,但是却让儿时的人们吃得那么美味!“阿娣太公”是待遇最好的一位,每餐一碗满满的小汤碗米酒,总是就着一点小菜,吃得有滋有味,红光满面,谈笑风生。那种惬意、那种满足,恐怕今生是再也没有什么言语可以描述的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依然是经济凋敝、生活困顿、物资匮乏的窘态。老底子永康人的传统——米胖糖和炒米粉,往往便是出嫁女孝顺爷娘的最好礼物。记忆中,小院里的老人们便经常拿这两样打点我们这帮小孩,而“阿娣太公”便是其中最慷慨的一位。
记忆中,“阿娣太公”的标志性衣着是一顶黑色可遮耳、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帽子。他总是红光满面、声音响亮,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拄着手杖。平时省吃俭用,突然有一天发了极大的善心,在乡里独资修了一条简易的石板桥。在遭遇一场洪水后,石板桥又重新修缮如初。这自然便利了去隔溪田畈劳作的村民。
用我妹妹的话说,我们这一辈人的称谓是最乱套的了。我也是莫名地感到奇怪,我们怎么会叫“阿娣太公”的儿子为“阿龙阿叔”的呢?许是上一辈人教诲的缘故,我们对人称谓便也是如此地牵名挂姓、有点不知大小。
“阿龙阿叔”在小院里是最有文化的一位,也是最有涵养的一位。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说话,不论大人小孩,总是一幅和蔼可亲的模样,透着一股干练和锐气,让人敬畏。那个时候,最会使坏的便是勇飞,穿了一双时髦的拖鞋,踢踏踢踏地响着,惹得我眼红了,硬是把一双好端端的凉鞋带给剪了,学了他的模样,引得他们一家人都哈哈大笑。多年以后,他们还曾提起这窘事,让我尴尬不已。而勇飞的二姐,生得清新秀气,模样娇小可人,天生的一副好嗓子,总是一大早在房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好听得让人以为是广播里唱出来似的。
而最“倒灶”的应该便是美秋了。她的外婆总是系着一条老旧的藏青色布腰裙,要她干这活那活的,厉声呵斥着,精瘦得有些骇人。因为没有经常一起玩耍,记忆里她的模样便模糊了。以至于后来我们上了学,她也回了自己的老家,少了音信,便再也没了一丁点的印象。
小院给人的总是那副老旧、邋遢的样子,走出去了,却总是有股不舍和依恋。时光如梭,岁月成河,过往的一切都成了梦中的记忆,成了念想。青砖老屋已是物是人非,黄泥墙的老屋头、亲人般的老邻前犹如心底里的一叶小扁舟,静静地淌在岁月河里,让我忍不住回头张望!
母亲的麦面汤
□王珍
对于家的眷恋,往往来自于对味道的怀念。每个人都会在心里装下一种特殊的味道,如母亲最擅长的红烧鱼,父亲最得意的酸脆土豆丝,奶奶独创的芋艿蘑菇等等。这些味道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却总在某个特殊的时候唤醒你对家的怀念。就如我总偏爱手擀面——俗称麦面汤,隔段时间就馋这口,这或许就是平时常说的情结吧。
我打小就对麦面汤情有独钟,却往往在农闲时才有机会等到母亲做这道美食。那时总喜欢在厨房跟母亲一起做。只见母亲先舀几升麦面到大盆里,然后加入一勺盐,接着一手舀水往里浇一手不停地搅拌着面,待到面全结成团,软硬适宜后再两手并用,使劲地反复揉压十来分钟,直至面黏性十足后就放在灶台上让它先醒一下。在旁边的孩子们早就剥好土豆切成大块放进钢筋锅里与大半锅水煮起来了。
已腾出手来的母亲就开始做浇头。先在铁锅里熬化一大勺白白的猪油装大碗,如果恰好有肉或者其他诸如胡萝卜之类的炒起来的话这浇头就特别饔了,浇头出锅,香味就在厨房氤氲开,不断刺激我们的味蕾。此外,还要在浇头碗里放入小葱、酱油、味精这些不可少的佐料。
母亲炒好浇头就开始擀面皮了。她一般先把面分为均匀的两团,再把一团面放到案板上用面棍用力地压,直到把面团压成扁圆后,才拿起约莫一米长的擀面杖开始擀面。母亲先在那团扁圆的面上敷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再继续用擀面杖压,直到面团成为厚面皮且能包裹住擀面杖,她才两手握着包着面团的面杖在案板上滚动,边滚边下大力使劲地拍打,面案随着母亲的双手用力发出“啪、啪、啪”的声音,母亲的汗也慢慢地渗满额头。伴随着面皮一次次地展开敷粉,一次次地包裹擀压,面皮不断地变大变薄,直至盖住整块案板。看圆圆的面皮已不到一毫米的厚度,母亲就两手拎起面皮的两头如叠被子般将它层层叠起,每层约十厘米宽,操起菜刀“嗒嗒嗒”飞快地切成一厘米左右宽的条,待全部切开,抓起面头一抖,长长一溜面条,薄而均匀,我们这些孩子在旁看得直咽口水。
待水开面下锅后,再抓两把家里腌制的雪菜扔进去再次烧开,热气腾腾中,面香土豆香雪菜香交杂着飘溢而出,令人垂涎欲滴。这时,先舀一碗热腾腾的面汤淋浇头上,葱油香扑鼻而来,守在灶台边的孩子们早准备好一只只大碗等着母亲盛面了。面盛出后淋上猪油浇头,再用筷子挑匀了,照例先给奶奶、父亲端一碗,孩子们就一人捧着一只大碗吃得滋溜溜响,奇怪的是麦面汤里的土豆块似乎也比平时吃到的香得多。母亲则继续擀第二团面,直至出锅装碗了才行。那时候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四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个胃口都大得很,特别是我,但凡吃麦面汤,一定会吃足满满的两大碗才过瘾。
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后,不免想念母亲的麦面汤,幸好当地多的是拉面馆,拉面虽然没有擀面这么薄,但也有手工面的味道,且看着大面锅上氤氲蒸汽的倒也可聊解思家之苦。工作后,单位附近有位可亲的娭毑,她的几个儿女全在外地创业,她就给常到她家玩的年轻人做好吃的,擀的麦面汤面皮薄而韧,面汤的浇头同样香气扑鼻,母亲的味道萦绕于唇齿间,令人眷恋。我就是在她家初次拿起擀面杖练习擀面的。
成家后到城里生活,永康城的大街小巷里倒有几家很正宗的麦面汤店,他们的招牌面——肉骨头土豆雪菜手工面吃着蛮正点,有时候就过去解解馋,但却总觉得还是少了点当年母亲的麦面汤带给我的诱人。我家那小吃货儿子更是常常反对我带他去这些面店。于是,我只有学着母亲的样子自己做。先和面,揉面,再把家里存放的鲜肉、香菇、青菜、土豆一股脑儿找出,炒了香菇肉丝、青菜做浇头。然后,把剥皮的土豆切片入锅水煮。家里没有大案板,擀面杖也是只有三十厘米长的一段,但做两三碗面的小面团来说绰绰有余的。为了能擀得薄一些,我还是把面团分成了两块。这样左一下右一下移动着让擀面杖在面皮上滚动,居然也把面擀薄了,厚薄均匀,与母亲擀得差不多薄。更欣喜的是,切面的时候居然可以叠加上好几层却不粘在一起,自觉也算是得母亲的真传了!待面出锅,加上浇头、青菜,热气腾腾的一大碗,儿子循着那诱人的香气而来,开心地大叫:“妈妈,好香啊!”
干干净净,再给我个大拇指:“好!”咳,原来这小子也跟我一样只喜欢母亲在家亲手做的麦面汤呢!初战告捷后,在家擀面吃渐成习惯。
写到此,忽忆起晋朝文人束晳《饼赋》(注:古人称面为汤饼)中的描写:“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强似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行人唾液于下风,童仆空瞧而邪盼。擎器者舔唇,立侍者干咽。”此文将冬日吃面解寒充饥的情景,写得生动而异趣横生,读之莞尔。想起在北方求学的儿子,在那个以面为主食的城市里,他是否能够找到一碗有家的味道的麦面汤,来抵御离家的寒冷呢?
鸡子酒
□吕丽盼
传统永康人家坐月子,必须实打实地吃上一个月的红糖鸡子酒,简称鸡子酒。哪怕产妇一天吃三顿,算起来也至少整整九十顿,用现在产后恢复的观念来看,简直无法想象。还记得老妈曾说起当年生下我后,每每到饭点,看着奶奶端着那碗鸡子酒向她走来就开始抹眼泪。那时候老爸出门在外,而新媳妇儿难免内敛,拒绝的话根本张不开口,更何况婆婆是真心为你好呢?好不容易回娘家了,第一件事就是嘱咐外公赶集时一定要买上两斤肉,回来烤肉麦饼吃。
尽管鸡子酒令产妇见了头疼,但若是难得吃上一回,也是人间之美味。鸡子酒做法简单,开火,倒入几勺红糖,一碗黄酒,若是怕酒味重,也可稍兑点儿水,待开锅后打入一双鸡蛋。待鸡蛋一熟,一碗香喷喷暖心又暖胃的鸡子酒就做好了。虽说做法简单,但原材料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红糖必须是本地糖蔗制成的土红糖,切不可取一般市面上甜菜制成的廉价红糖;黄酒则是自家用红曲糯米酿造的陈酿,香味儿更足;讲究些的,这鸡蛋也必须是自家喂养的土鸡下的新鲜鸡蛋。一口鸡蛋,就上一勺飘着浓香的红糖黄酒汁儿,就别提有多美了。
在永康,鸡子酒向来被视为大补之物,虽说不是产妇专供,但在二三十年前,可不是随便能吃上的。家中谁有个感冒头疼的,兴许还想不起煮个鸡子酒补补,但若遇上谁病了几天,眼看着身子虚了,家里的主妇便会提议:“替你烧碗鸡子酒来哦?”当然,除了补身体,好东西自然也是待客之物。刚吃了饭去别人家做客,也有主人家会给客人煮上一碗鸡子酒,算是加餐点心。如今看来,也算一道快手的饭后甜品了。
几十年前,物质条件差,去别人家做客若是吃上了一碗鸡子酒,回来都值得跟邻里间说道说道。记忆里,最近一次吃鸡子酒,也已是十年前了。那年年初去姑婆家拜年,为了不让年迈的姑婆下厨烧鸡子索面点心,大家特意挑了晚饭后去。姑婆一听都吃过饭才来,心有不悦,立马站起来说:“那我给你们烧碗鸡子酒,这个不占肚,红糖是我儿子做了给我的,酒也是自家做的,鸡蛋是人家给的土鸡蛋,都好的。”转眼姑婆已是耄耋之年,下厨之事鲜有谈起,可那个冬夜姑婆端来的那碗香甜暖人的鸡子酒,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味蕾上。
尽管如今仍有不少产妇依旧沿袭着月子里吃鸡子酒的风俗,但在主妇们的待客清单上鸡子酒却慢慢消失了。时至今日,你若在永康去谁家里做客,如果主人家还能为你烧上一碗鸡子酒,那端出的不仅仅是一份好客之道,更是对永康饮食文化的深深眷恋之情。